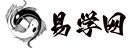齐一民《寅虎卯兔集》上部(19)芭蕾舞《过年:中国版〈胡桃夹子〉》超然印象
芭蕾舞《过年——中国版〈胡桃夹子〉》超然印象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晚,天桥剧场

《寅虎卯兔集》,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第1版。
既然著名舞蹈大师、中国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老师让我说说对这场戏的看法,就不敢怠慢,回到家立马准备写评论,但看过剧照后我发现评论是多余的。这部戏在千禧年,也就是二十年前就在北大百年讲堂首演了,说什么都已经是多余,因此应该把以下的文字看成观剧的印象。
对这部戏的印象还是挺特别的。特别之一是它的剧名《过年——中国版〈胡桃夹子〉》,这是印在剧照上的,剧场里灯光打的则相反《中国版〈胡桃夹子〉——过年》,这无疑不妥,一定要倒过来,因为我猜想来剧院看戏的观众百分之九十以上不知道什么是《胡桃夹子》。您看那些很多是小演员的爷爷奶奶们雪花白色的头,就知道我的猜想肯定有理。回家后我问老伴:“你听说过《胡桃夹子》吗?”答曰:“是一首唐诗的名字吧!”这更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当人们不知道你说的中国版的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的剧名就是无效的,因此我建议尽快将剧场里的字幕像剧照上那样颠倒过来。
细节决定一切,尤其是细节决定你的观众记得住记不住剧的名字的时候,那细节就已经远大于细节了。
这个剧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是全场使用的音乐竟然是柴可夫斯基原装的曲子,而且是百分之百现场演奏,至少这对于我是头一遭。那么你可以尽力发挥想象,比如将《天鹅湖》的原曲排成个中国版的什么剧,排个“欢度中秋”咋样?还有,假如外国人也如法炮制,用中国神曲《梁祝》《黄河协奏曲》为伴奏演一台俄国版的、法国版的什么舞剧,比如说过圣诞节、万圣节之类的,演员再穿上他们的西装或戴上白色假发,那会是怎样的效果?想,继续想,往细节想,于是,我想到用什么瓶子装什么酒的问题。老柴的乐曲无疑是瓶XO,咱把瓶子拿来后朝里面倒进茅台或二锅头,那酒的外观无疑是好看,摇摇,动静也好听——是啊,谁能比老柴更会谱美妙的乐曲呢?但那酒咂摸着味道就有些不伦不类和稀奇古怪了。今晚的观剧效果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地养眼,中西合璧嘛;那么地绚丽,演员们花枝招展嘛。看剧时耳朵在享受着老柴乐曲在指挥张艺棒下的舒朗柔美,眼珠在扫描着那么多俊郎靓女功夫超凡、青春气息浓郁的翩翩舞姿,中华美的因素、西洋美的因素乃至印度美的因素,青年演员、少年演员乃至少儿演员,简直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包裹在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包袱皮中的鲜花和彩带,一层层地打开,一件件地展示,世界上哪有这等高端的享受?这样的视觉盛宴和听觉按摩,你怎能不醉陶陶、不喜洋洋、不乐呵呵呢?
然而,享受归享受,艺术分析归艺术分析,感官归感官,理想归理性,我在想:为什么这种改编给人的感觉怎么都不像是一流的艺术作品呢?
说到老柴,说到他给《天鹅湖》和《胡桃夹子》谱的天衣无缝的神曲,很久以来让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美妙的舞曲究竟他是看舞蹈家跳舞后谱的,还是他先谱好曲别人再依据他的乐曲编的舞呢?
这个问题在今晚观看《过年——中国版〈胡桃夹子〉》时或能引发再次提问和核实。显然,我们中芭是先听曲子再配舞蹈的,这毋庸置疑。那么好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听了神仙的曲子就能想象和派生出这么一台美轮美奂的艳舞而不是其他不堪入目的东西?没错,你听过马路上嘈杂声音之后绝不会想象出今晚舞台上的这些美丽画面。我真正想说的是:今晚的主角和灵魂其实是俄罗斯人老柴。老柴的《胡桃夹子》是我们再也制造不出来第二个的魔法瓶子,我们是在按照它音符的编排再造着一台被改装了的“中式美梦”,而台上那些舞蹈家华美的舞姿就是那个美梦的零配件,一句话,调子是先人定的,我们是在再次阐释,我们在接续着伟大作曲家早已制定好的格局,填充今天的、我们的中华生命元素。
舞蹈家和作曲家都伟大,但作曲家伟大在先。
今天恰逢北京语言大学六十甲子校庆,因此今晚在北语毕业生、现在在中芭就职的周超然同学的热心招待下,我能陪伴老领导刘和平院长一同度过疫情期间极为罕见的有现场乐队伴奏的中芭舞蹈《过年》。怎能不怀着过年一样的享受和内心的超然呢?要知道我过去两年去过的国家大剧院跨年音乐会,就是由中芭演奏和张艺指挥的呀!
(未完待续)